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没有家,没有电影
当我计划为比利时导演香坦·阿克曼(Chantal Akerman)今年的片子《无家电影》(No Home Movie)写篇文章时,一个念头闪过,影片的名字让我想起罗兰·巴特最后一本书《明室》——两者都为哀悼逝世的母亲而作,又同时关乎一种艺术媒介的特性。一个星期后当阿克曼自杀的消息传来,这个念头竟然成为了这样不详的预感。《明室》在法国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巴特去世;《无家电影》八月初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放映,当时评论褒贬不一,阿克曼的死也是在这之后不到两个月,距离片子在纽约电影节的首映只有两天。他们两人都在最后的作品里空前地袒露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他们的死似乎暗示了对普鲁斯特“成为作家(艺术家)”式元叙事的一种不可能的尝试。或者说,他们选择的媒介没能帮助他们度过哀悼的痛苦。在写作《明室》时巴特感到“被两种语言撕扯,一种是表达性的,一种是批评性的”。那张对他而言极为重要的母亲五岁时的照片,为他证明了“不可能有关于摄影之独特存在的科学”[1] 。而阿克曼超过四十年的电影创作总是在虚构和非虚构的形式之间进行着复杂的协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欧洲与美国的混合物”[2] ——她受到的影响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国实验电影,法国新浪潮故事片,以及新小说的“科学性”语言等。一个更具共时性的对照是意大利导演南尼·莫莱蒂(Nanni Moretti)今年的新片《我的母亲》( Mia madre),同样关于失去母亲的哀痛,也刚在纽约电影节首映。这部半自传电影用高度戏剧化的方式讲述一位左派女导演玛吉莉塔如何挣扎着同时应对事业危机和病衰中的母亲,莫莱蒂本人饰演她哥哥。这部影片的情节发展主要依靠一名来自美国的浮夸的演员来推动,他在玛吉莉塔拍摄的电影中扮演着一位工厂厂长,需要应付工人们的罢工。《我的母亲》明显地指涉了好莱坞对莫莱蒂的压迫性影响。然而,主角玛吉莉塔作为导演和女儿的二重身份叙事之间并不存在交集,因此哀悼过程与电影媒介本身相互独立。
除了一组荒凉的以色列风景片段,还有两段对母女用Skype打视频电话的记录,《无家电影》几乎全部由阿克曼的母亲在她位于布鲁塞尔的公寓中的日常生活片段组成。大多数阿克曼的私人化或非虚构电影可以被理解为她的多重自我与两种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种是兼具保护性和限制性的室内空间,一种是延伸中的城市或自然景观。她是构建电影空间的大师,革命性地用空间再现极简主义情节中的时间。她强调人的自我与对私人和公共空间的知觉和概念息息相关,更重要地,她揭示出这些空间是如何被性别化的(gendered)。这一次在《无家电影》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她以往的实践方式: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碌,如同《我的城市》(Saute ma ville, 1968)和《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1975);从公寓窗子向外观看布鲁塞尔的街道,就像她在《在那里》(Là-bas,2006)中从房间的窗子往外窥探特拉维夫市的一个街坊;从移动交通工具上拍摄以色列的风景,她曾用同样的方法拍摄《家乡的消息》(News from Home, 1977)中的纽约街道;在两个长镜头里,她手持摄像机分别在夜晚和白天绕着母亲的公寓走了两圈。这让人想起她如何用摄像机检视各种临时居所的空间结构,比如《房间》(La Chambre, 1972),《蒙特利旅馆》(Hôtel Monterey, 1972)和《你我他她》(Je Tu Il Elle, 1974)。但是在《无家电影》中,连接她自身和各种可能的家/家园的尝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徒劳:她的母亲在厨房缓慢走动,发出沉重的喘息;布鲁塞尔的街道看似触手可及,而三天里的唯一一次外出散步便让母亲精疲力竭;伴随着荒无人烟的以色列沙漠,我们听不到阿克曼朗读来自家乡的信,只有风声和车辆在沙砾上行驶的声音,画面拒绝了任何乡愁的可能性。这些沙漠的镜头也组成了阿克曼今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八屏录像装置《现在》(Now, 2015)。在展场能听到阿克曼在原有的音轨上加入了呼喊,引擎和枪击的声音。在这个名为“所有世界的未来”的群展中,阿克曼无疑在批判当前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的军事及政治立场。如果说阿克曼通过以色列沙漠的影像质问着人们对家园(homeland)空间的暴力扩张,那么她对母亲公寓空间的影像重建则拷问着家(home)的概念,这个储存家庭记忆的时间性场所。与人们通常对家庭电影(home movie)的印象不同,这里的数字影像完全没有承载过去时光的质感。更为甚者,有两次她故意“错误地”设置摄像机的曝光度,让欠曝的昏暗房间里只有不可辨认的黑暗人影,在阳台上只有过度曝光状态下的一片亮白。这些时刻催生了关于家庭电影这个形式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观看另一个人的私生活时,观众期望电影为他们暴露什么样的内容?在阿克曼的摄像机下,那儿放佛没有家,也没有电影。
电影学者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在她的文章《朝向一种非虚构电影经验的现象学》中为主观的电影经验描画了一条光谱,在光谱的两端分别是家庭电影和虚构电影,而纪录片则处于这两者之间。从家庭电影逐渐过渡到虚构电影,观众的意识愈加依赖银幕给予的信息,并参与构成愈加脱离自身经验的自主的现实世界。对索布切克来说,家庭电影中零碎而具体的影像所持的特殊感动力并不来自对真实经验的再现,而是它其中蕴含的“无可挽回的失去”。因此,“让一个女人感伤的家庭电影是让另一个女人无法满意的纪录片。”[3] 在索布切克光谱的一端,阿克曼的家庭电影似乎更让人困惑而非无法满意。《无家电影》在纽约电影节的最后一场放映中,整场的观众同时哀悼着阿克曼和她母亲,这双重的“无可挽回的失去”,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放映结束后,一声试探的掌声很快被沉默熄灭,片尾字幕结束得太快,每个人都犹豫着,不确定是否应该离席。这也许是他们(包括我)第一次在这样正式的场地观看这样“原始”、没有任何叙事的家庭电影。在索布切克光谱的另一端,莫莱蒂的虚构故事的最后,美国演员终于成功地诠释了他的角色,这标志着女主角玛吉莉塔的艺术家身份得到确认;她最终对母亲离世的接受,也标志着她作为一个女儿的主体性的最终完善。这个故事不坏,但无疑它是安全的。由此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对艺术家而言母亲的死这样危险,以致巴特和阿克曼都无法熬过这一关,莫莱蒂则需要虚构一位女性形象来替代自己?(因为女性的混乱情感状态更具可见性?)
当一个艺术家的自传性文本里出现彼此冲突的关于自我的多重叙事,一般而言艺术家会最终落脚在一个“作为艺术家的自我”这样的叙事中——这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总体叙事(就电影来说,我脑子里想起的是阿涅斯·瓦尔达在自传《阿涅斯的海滩》的最后端坐在一个自己用胶片搭建的“电影之屋”里)。在阿克曼的整个艺术生涯中,她持续地关注着各种身份问题,包括女性、性向、国族和跨国移民等等。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身份问题都与阿克曼和她母亲的关系有关。一段轶事也许最能说明她同时作为一个女儿和电影人的挣扎:她在墨西哥放映《奥迈耶的痴梦》(Almayer's Folly, 2011)时有场问答环节,她的母亲也在场,由于耳背她什么也没听懂,但是在活动结束后她对阿克曼说:“你拥有所有那些,而我只有奥斯维辛。” [4]不止一次阿克曼提到过她的自身存在很难超越母女关系:
我出生在1950年;我的母亲在1945年离开集中营。我一出生就是一个老婴儿了,因为我母亲的悲伤需要占据所有的空间。还是小孩的我就感到了那种悲伤,所以我不能愤怒。我必须保护她。在和她的关系之外我无法存在。还有几个月我就要60岁了,而我现在才能把“我”字说出口。一年半以前,我终于意识到我是愤怒的,就像个需要一场革命的15岁小孩。除此之外,我非常爱我的母亲;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种逃避和隐藏愤怒的方式。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我无法作为女人存在。她有悲伤,所以我无法悲伤。她受到伤害,所以我不能尖叫…如果不是电影,我早就死了。[5]
阿克曼的成长被她出生以前的叙事支配着。无法被理解的创伤事件笼罩着上一辈人的故事,也抽干了她自己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对阿克曼来说,电影创作是她去成为的方式:通过电影,她成为女人,成为一个能悲伤的主体。在制作《安娜的旅程》(Les Rendez-vous d'Anna, 1978)时她尝试获得一种电影层面的救赎。影片中奥萝尔·克莱芒(Aurore Clément)扮演的安娜是一名导演,出差的旅途中在一个火车站与她的母亲见面,并和母亲在酒店度过了一晚。三年没有见到女儿,母亲的第一句话是欢快的“你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在睡觉之前,安娜在母亲充满爱意的注视下脱去衣服。躺在床上,安娜向母亲吐露了自己最深的秘密——她爱过一个女人,并和她发生过关系。而后母女俩一起回忆起旧时光,安娜说起童年时对母亲的女性气质的深刻印象。第二天早晨在登上离开的火车前,安娜跟母亲道出“我爱你”。那时候阿克曼就走在时代的前面,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义学者如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等开始修正弗洛伊德传统下的男性中心的精神分析范式,强调母女关系对性别差异和女性特质的根本性影响。今天再度观看《安娜的旅程》让人难过——阿克曼在真实生活里一直没能获得女性主体的独立性,要取得这种独立性,她母亲的认可必不可少。但在《无家电影》里,母亲的回忆中,阿克曼还是那个“有着漂亮眼睛的小女孩”,她唯一一次谈及阿克曼的身体,也是小女孩时的阿克曼脏兮兮地回家,她拎起阿克曼去洗澡。有一次阿克曼不在身旁,摄像机记录下了母亲在饭桌上的话:“她(阿克曼)爱说话,但是从没说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有一个让人心碎的镜头:母女俩在Skype上打视频电话,对着电脑屏幕的摄像机忽然朝视频里母亲的一只眼睛推进,我们看到的是放大后的低像素数码图像,只有一片扁平而模糊的黑色,看不到任何倒影。这也许是阿克曼最后一次用电影艰难地寻求着母亲的认可。影片中还有一幕,在摄像机之前,阿克曼拿着另一部DV,一言不发地拍摄着昏睡中的母亲。这可以被视作她尝试用导演身份重写女儿身份。但这也加剧了影片完成后她的痛苦,认为自己背叛了母亲,感到“有罪”。
对比之下,莫莱蒂的电影集中关注的是女儿的经验,母亲那抽象的“病中的身体”成为支持女儿个体化进程的一个客体。女儿主体性的出现也紧紧依附于对母亲的“他者化”(othering)。影片没有提及母亲对作为左派导演的女儿的任何影响[6] 。对照阿克曼终生不懈的努力,莫莱蒂虚构的女性代理人更像是一种男性的幻想。
如果我们把阿克曼的死归为集中营幸存者后代常有的抑郁症状,那实在是过于容易了。如果父母的离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是谁,那么一位艺术家的死应该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艺术媒介的制度性结构。非虚构电影从诞生起就一直束缚于人们对它的客观性诉求,需要它是完美的观察者和证据提供者。纪录片一直被历史性地与科学和新闻报道联系在一起,创作者的主体性被视为对纪录片的社会和历史再现的污染。在洛迦诺电影节的放映后,阿克曼被指“任性”、“自恋”,而这时观众正是一名自传性作者“最必要的他者”,观众是最后一个能包容并修复她的主体性的话语空间。在八月中的一篇访谈里,阿克曼谈起在洛迦诺的经验:“在那里的巨大的人群,他们能毁灭你。”[7] 纽约电影节的策划人飞快地把《无家电影》首映那天弄成了一个“感人的夜晚”,他致辞道:“与人们所说的洛迦诺的故事正好相反,我认为那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而不是停一停,反思一下艺术电影的制度性生存环境,这些国际电影节恰恰集中体现了这种本质上为男性的制度,在这个制度环境里阿克曼的电影找不到归宿,它也是一部“没有家的电影”。男权的制度性结构不仅限制着女性,同时也限制着男性。巴特思考着现代社会对哀悼的忽略,曾反复提到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中的句子:“一旦我开口,我表达着普遍性,而当我避免开口,便没有人能理解我。”[8] 巴特谈论摄影的写作,尤其是他的“刺点”理论,现在仍然被批评过于主观。他离世的十年后,英国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仍然只看重他早期的符号学著作,他后期更私人化的作品被批评为“边缘的写作,缺乏让人满意的作者权威”——多么熟悉的话。
1.罗兰·巴特,《明室》,Hill and Wang出版社,1981年,71页;
2.见The Criterion Collection对阿克曼的访谈“香坦·阿克曼谈论《让娜·迪尔曼》”,2009年;
3.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朝向一种非虚构电影经验的现象学”(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Non-fiction Film Experience),《收集可见证据》(Collecting Visible Evidence)Michael Renov & Jane Gaines编。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249页;
4.见Daniel Kasman的报道“香坦·阿克曼谈《无家电影》”,2015年8月17日;(//mubi.com/notebook/posts/chantal-akerman-discusses-no-home-movie)
5.见Melissa Anderson对阿克曼的访问“她光辉的十年”,2010年1月19号;(http://www.movingimagesource.us/articles/her-brilliant-decade-20100119)
6.莫莱蒂的母亲曾辅导我的一个来自罗马的朋友拉丁文多年。这位朋友告诉我她时常鼓励他成为一名“有机知识分子”,鼓励他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
7.同上,Daniel Kasman;
8.罗兰·巴特,《哀悼日记》,Hill and Wang出版社2009年;71页。
2 ) 空空之响
观影过程,数次暂停起身吃水果、刷手机,趔趔趄趄看完…电影、纪录片、家庭录像?观众该带着什么样的预期来观影?还是都不该做假设。 漫长无意义的空镜头早已超出阐释。盯着屏幕发呆走神时,镜头反倒像在盯着我,而我试图在镜头给定的有限视域内搜寻一些什么信息,或期待有什么人物闯进来、期待下一幕会有几段特写,却通通没有。 如果不是变幻的车流、脚步声,还会以为是否影片卡住或误按暂停。在这稳定不变中感受到强流动的镜头,尤其是在行驶的戈壁景象那段,似乎被提醒了某种本源的状态,即一位观众(或作为一个人)不能转身、也不能回头,只能眼睁睁看所有事物倒退流走的那种恍惚。带着这样的观察基础,也会发现一片看似定格的草场,上空的云会悄悄移动变幻光影。故在此种缓慢流动中,时间如花凋落,如香特尔母亲仙逝。这部乍看无情节、非故事的纪念册里,有母亲行走收拾动作之中不时的哼哼声、视频通话中明明说过有事挂断但还又继续聊下去的依依不舍、有担心母亲睡着而提出让母亲讲故事的请求。当然,最令人心碎的是母亲意识到香特尔虽侃侃而谈但隐约有些话藏在心底,而香特尔阿克曼在该影片上映同年2015年自缢。 空荡荡的镜头,好像只能握住一丝香特尔阿克曼留下的沉默。
3 ) FIFF16丨DAY1《非家庭电影》:给家庭的最后献祭
第16届#法罗岛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非家庭电影》,下面请看前线血脉成员们挥别人生的评价了!

大钊:
纯正的home movie。
松野空松:
既私人又共通,片名中Home一词包含文学创作中最常用的两种含义。
米米:
母-女的关系确实是种很特殊的存在,很多时候真正失去了,才会发现,原来一直爱的......不够多。
空地:
事件发展本身对于拍摄工作的进程是破坏式的,也许本意是续写家庭美食与哲学,而结果呈现为了意志的消沉。
Not Here:
没有过分的举动,也没有过轻的动作。其实这一部我觉得很可惜,如此私人化的影像似乎需要更独特的表达形式。
法罗岛帝国皇后:
衰败是有感染力的,私密的家庭寒暄靠镜头纪录成公开的遗书,思念二字牵连老母亲和香特尔地理上忽远忽近的心。
Pincent:
熟悉的家庭空间可能充满孤独,或者说真正的家从一开始就没有。关于距离也关于交流,关于孤独也关于亲密,关于爱的记忆也离不开疼痛和沉默。以静态的镜头呈现时间和必定的衰败,开场是大风,告别是静默。
飞檐:
在一种类似幽魂的视角的窥视中,似乎完成了生者与故人的对视转换,漫长又未经雕饰的空景像母亲灵魂的注视,也是她作为女儿在接受离别和没能真正接受之间的放空。以这样的方式组织片段似乎在开头就已经倒置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像她永恒的依恋。亲情动人在未经预设的生活对话里,没有指向和头绪。终于在这种远距离的凝视里,清醒地认识到了真正的生死离别,结尾太有力了。
子夜无人:
用家庭录像来反家庭电影,镜头作为承托生命体验的最后防线,看着一个老人从谈论年轻岁月、说起如今的自己从头到脚都已经泛白,然后到下一刻她更老了,老到动不了、笑不出、说一个字都累得吃力。对于生命衰败迹象的记录,惊悚到让人脊背发寒。一个鲜活存在过的人,她所有丰盛灿烂、痛苦沉重的记忆,终有一日会变成阳光穿堂的空屋、大风盖过的荒原。满室的沉默不语、烧成灰的离离山野,都是你,也都是我。
DAY1的纪录片单元场刊将在稍后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4 ) 属于阿克曼的个性化叙述,个体化的历史记忆,深度亲密的母女之情
看后久久不能平静,阿克曼用非常个人化的记录方式,看似琐碎的家庭镜头,实则有内在深层严密的逻辑,和母亲之间的对话亲密感人,充满爱意,感动于和阿克曼视频通话时妈妈疼爱的一声声宝贝亲亲“每次见到你,我都想抱紧你”,这也呼应了《家乡的消息》中母亲来信的内容。这样一位从集中营生还的母亲,如此疼爱女儿的母亲,个人的生命记忆中深深地印刻着苦难的历史记忆,民族历史具体化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从家庭的记述延展到了国家。
母亲身体状况良好时,影像里的家明亮舒适,大多是近距离拍摄的母亲的正脸,而母亲病情加重后,以中间经过一段黑暗中紧张、快速移动的镜头,和镜头外的喘息声作为暗示,而后不再将镜头直接对准母亲的正脸,家里的画面也多处在傍晚的昏暗之中,之前母亲和阿克曼有说不完的话,总舍不得挂掉电话,而病情加重后的母亲只想躺着,已经没有聊天的力气,但她依然记得阿克曼要离家,对她说:“我真想每天都见到你。”
阿克曼自由地运用着镜头表达,将内在的情感显现于独特的镜头语言之中,如此细腻深刻,让人见识到了电影的更多可能性。
5 ) 所拍即所见
看到一半要去上课于是分两次看完。巧合的是上课的内容恰好关于纪录片的意义:展现所见的一切,所拍即所见。
将近两个小时和妈妈的琐碎日常,不少还是(看似)无意义的空镜头。和妈妈视频时候妈妈说“每当这时候我就想抱紧你”让离家几千公里外的我鼻头一酸。影片最后,背光的昏暗的沙发里妈妈说“我想每天都见到你”,唉。和妈妈谈论一切,从家长里短到犹太纳粹,妈妈讲话很慢却有很多话要说。每一段对白后都放一个/组空镜头。最后一幕,熟悉的客厅不再有人走动,空空荡荡,只有环境音,留下无限感伤。
纪录片课上提到的一切元素都在这里得到完美展现:sans mise en scène, sans scénario, sans voix off, plan-séquence.. 稀松日常+不完美footage 边看边告诉自己yes you can do it 但同时不能满足于把这个当标杆哈哈。纪录片除了展现真实,也是拍摄者或者说导演本身一种思绪的表达。可有时这些思绪并不清晰,于是只能展现所见。也许你所想不是我所想,没关系,我所摄即我所见,我要传递给你这种气氛,这就够了。纪录片更像是被无限延长的静止照片放映,只给耐心的人看,因为在你失去耐心的一瞬间相片就发生异动,这就是生活带给你的惊喜。
“自杀前的遗作”这个title给影片笼罩上一层忧愁气息。这是我第一部香特尔,爱上她,加一星感谢。
6 ) 香提尔·阿克曼的真正主角
《无家电影》(No Home Movie)并不是香提尔·阿克曼关于她和她母亲关系的第一部电影,但却是最后一部。这种最后的意义是双重性的,影片在母亲去世后才开始剪辑,于2015年10月5日在洛迦洛电影节公映两个月后,65岁的阿克曼在巴黎自杀离世,《无家电影》成为香提尔·阿克曼的遗作。至此,我们失去了那个25岁就拍出了女权主义大师级作品《让娜·迪尔曼》的天才少女,她曾用自己的镜头审视着女性,也审视着电影本身,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在她的作品中被打破,又以“结构电影”的形式重新组织起来,这是阿克曼的敏锐与才华,她把人物放置在线性无限延长的时间和空间中,又赋予时间和空间以凝固的形式。当时间和空间在被放大中涨潮的同时,人物的姿态与行为、影片的叙事与戏剧冲突都呈现出退化的姿态。时间和空间,则成为阿克曼电影真正的主角。
比“不久”的时间更长
在长达115分钟的《无家电影》里,除了长久凝滞的空镜头外,几乎就是香提尔·阿克曼的母亲在她公寓中的日常生活:吃饭、喝水、打电话、发呆。从短片处女作《房间》就开始建立的实验电影形式,仍然在这部记录母亲的影片中被应用,我们同样也能在其代表作《让娜·迪尔曼》中看到这种时间无情流逝来带的震撼性——妓女让娜·迪尔曼在三天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家务劳动后,杀死了自己的客人。阿克曼用几乎凝固的摄影机表达着她对时间的理念,这是她与戏剧性电影和叙事性电影的根本不同。
经典好莱坞在创造了“透明性剪辑”之后,时间便在电影中被压缩,成为服务于叙事的工具,或者是玩弄技巧的噱头,电影在带来奇观体验的同时也让我们在观影时无法觉察到时间的流逝,与此同时,我们的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电影夺走。但在阿克曼这里,唯有连续的时间是值得被表现的真理与现实,她打破了古典故事片为我们精心建立的“真实幻觉”,流动的时间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真实,时间的流逝在观影中成为可被感知的、切实存在的线性尺度。在这个角度上,阿克曼与布莱希特所宣扬的戏剧理论站在了一起,成为了商业电影、经典好莱坞以及传统纪录片的对抗者。
影片中,阿克曼的母亲在固定的镜头前走来走去。她时而远离镜头站到窗边;时而对着镜头背后的阿克曼说话;时而丝毫不理会镜头的存在,紧贴着镜头走过。冗长的固定镜头沉闷压抑,但同时也在运动着,我们通过母亲的动作得到了在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间来回切换的景别,也得到了母亲的生活真相。
正如阿克曼自己所说“要把摄影机放在那里,放在我的面前,等够必要的时间和真相出现的时候”,时间流逝的被感知,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阿克曼极具个人风格的镜头处理,大量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在影片中被使用,使得影片段落所表现的时间与观众观影时间相等,但凝滞的场景却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拉长。观众焦躁不安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却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真相的出现”,并通过等待与观看感知人物与自我的存在。
我们一定会用“长久”来描述阿克曼的镜头,但“长久”却只能在比较中获得它的定义。那些短暂的、叙事性的、描述动作的短镜头与快速剪辑显然是瞬时的、短暂的与“不久”的。与它们相比,阿克曼比“不久”更久。她在电影中还原了时间的长度,让观众对时间产生敬畏与震撼。时间不仅存在在场景之中,还存在在银幕对面看着它的观众之中。
空间的封闭与延展
阿克曼15岁离开故乡,奔赴法国求学,此后又辗转纽约。故乡的意义对她来说含混而模糊。母亲的所在地是故乡在物理上的存在,然而被阿克曼所舍弃的比利时却失去了作为故乡的意义。阿克曼将这种含混展示为封闭的寓所和开放的外景空间,影片拍摄的公寓并不是阿克曼儿时长大的“家”,母亲则独自留在这个女儿不在、也没有旧日回忆的公寓里。“家”的意义因为女儿的离去、丈夫的缺席、回忆的匮乏而被消解,它承载的情绪、记忆、意识均被抹去,它成为了填充摆设和家具的容器。
寓所作为家的实体承载空间,被现代派的先驱波德莱尔解读为孤独的场所,这种孤独在阿克曼这里同样得到了验证。家,作为一个封闭的实体空间,提供给拥有完整家庭关系的人保护的港湾,但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隐蔽和私人的场域。每当我们走进寓所、走进家庭,在受到隔离外界的保护的同时,也必须面临失去交流的孤独。
阿克曼用场景中的垂直线条强化了这种空间的封闭感:母亲吃饭的厨房里竖排的厨具柜,直线的桌脚和凳脚,封闭垂直的门框线条,无一不传达出“家”这个空间对母亲的禁锢。在母亲离开镜头的视线以后,镜头依然凝视着无人的房间,只有家具和陈设面对镜头的审视,“家”的意义彻底被抹去。而母亲,在影片的时间里,也从未走出这个封闭她的“家”。
但是,仅仅的空间封闭并不具有革新性,与对时间的重新构建相对应的,阿克曼把延展性给予了这些封闭的空间,在那些固定而耐心的镜头里,阿克曼为我们展示了生活中被忽略的点点滴滴:掐灭的烟头腾起的烟雾,被风挥动的百叶窗,甚至还包括长时间谈话场景中室内的明暗变化。我们得以在长时间的镜头记录中去发现那些我们未曾发现的空间变化,将空间延展。同时,阿克曼还坚持了她在公路电影《安娜的旅程》中使用的直线运动镜头,让镜头在公寓的房间中“直来直去”地巡视,持续又谦逊地将空间放大,这种被电影史学家波德维尔称之为“极限主义”的风格,在稀疏的情节叙述中严格而克制,构建出不同于常规叙事电影的真实空间。
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说,“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家,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那么同样的,家宅也应当庇佑着可能性,不论是故乡还是他乡,不论是封闭与开放,阿克曼都打开了这种可能性。
不在场的女儿
作为女性主义电影的先锋,阿克曼以她的冷静与超然获得了电影史的垂青,但在她的影像中,女性始终是被禁锢的,她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谱写女性受到的困境,也表达自己的困境。作为女儿,母亲成为她始终无法回避的议题。片中,无论是她自己和母亲的对话场景,还是隔着电脑与母亲使用Skype视频通话,阿克曼都没有使用正反打镜头。事实上,她在一贯的作品中都明显脱离了正反打体系。她所需要的是来自摄影机背后的自己作为导演的视点,而非剧中人物的视点。正反打的被丢弃,使得阿克曼自己与母亲从未真正的在画面上“同时”出现,阿克曼本人也从未在影片中出现正面和完整的个人形象。有的,只是被画面切割的肩部以下的身体、落寞的背影、看不见脸的侧影。以上种种,都揭示了阿克曼的“不在场”状态。在拍摄与被拍摄时,这种“不在场”体现得更为明显。片中,母亲躺在在沙发上,穿着粉色睡衣的阿克曼拿起DV从摄影机前经过,拍摄着小憩中的母亲,而她自己却被着家具遮挡着。DV拍摄着母亲,摄影机和观众则“拍摄”着正在拍摄母亲的“不可见”的阿克曼。形象和影像上的残缺造成了母女关系的间离,她们被拆分、被隔开,成为彼此缺乏联系的个体。
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阿克曼内心困境的写照,沉迷于电影的她年幼离家,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缺席的存在,“家”也因为她的离开而成为“无家”。同时,作为女儿的她无法从母亲这里获得真正的认同,也就无法确认完整的自己。母亲在与小女儿西尔维娅聊天时说:“香特尔从来不真正和我聊天,她从来不告诉我重要的事”,对此,走出了镜头外的香特尔以画外音的形式回答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片中最为让人动容的场景——阿克曼在和母亲视频通话时,母亲的脸填满电脑屏幕,镜头突然对着电脑屏幕推上去,靠近了视频中母亲的眼睛,影像变成了一团模糊晃动的马赛克,阿克曼透过镜头凝视着母亲的眼睛,此刻,导演作为女性的敏锐感触和亲情冲动,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拍摄方式呈现在屏幕上,打动了观影中的每一个人。
在《无家电影》最后的聊天中我们得知,阿克曼的母亲曾经进过集中营。走出集中营的她对这段经历只字不提,只在一次阿克曼的电影放映会后对阿克曼说:“你拥有所有,而我只拥有奥斯维辛。”母亲的苦难留在过去时间的某个节点上,而无限流动的线性时间却把苦难移植到阿克曼身上,转换为她作为女性的焦虑与恐慌,并通过胶片流向银幕。因此,坦言自己从未走出母亲对自己的影响的阿克曼,不仅是在为母亲发声,也是在为自己发声。从这个意义上,《无家电影》这部影片反而将这对被分裂开的母女黏合在了一起,但对于观众们来说,则是永恒的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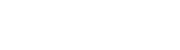




















除夕夜重看。当DV撞上屏幕,水面,Chantal显影。拍母亲,也是拍自己。最后逸出的视角不知是母亲的魂还是女儿的影,私影像变成“公影像”,再无Home Movie。母亲谈起她小时候,让人不禁想起Saute Ma Ville里她脏兮兮的样子,想到这就哭了起来。
当然简略、粗糙、不伟大、随意、平庸,依赖作者的神话;但观众也选择作者。跟随阿克曼,在每一个镜头里看到自己所看到的,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陌生和熟悉的家庭空间,在瞬间生成记忆:我们记得;家不再是家,但这是家。浓烈的、浓烈的热爱
绝非散漫的记录,而是提供了一种由私影像过度到公共记忆的可能性,日常谈话中的家庭史被包裹在历史尘埃里,从来不曾被忘记,且更深刻地镌刻到每个人深层的记忆之海,在自然的接话段落中伤口被一寸寸暴露——这种无根感如此深而狠,不止是个人的体验,也是民族群体的症结,局外人很难以任何立场去审判。因而是否可以认为,与母亲的深深眷恋之情,放大则是和母国文化的无法割舍,母女互喊“宝贝”好甜啊,令人泪目;母亲安好时厅堂敞亮光线明朗,镜头一转从巨幅白色急转到黑暗如洞穴的客厅(此手法在她作品中屡有出现),此时母亲已然衰弱,直到最后一幕拉上窗帘如同宣告向全世界落幕,而观众很难判定此时视点的主体究竟是谁,幽冥感冷彻全身。空镜的时间凝化功能——被风吹歪的树,花园里倾颓的椅子,茫茫的连绵山丘;室外运动+室内固定。
“I want to show that there is no distance in the world”而又“She never tells me anything important”这不正是我们每天所面临的绝大多数困境么
哎呀!看的我都睡着了~
对于阿克曼而言,母亲的去世就是终点,这是毫无疑问的,电影如狂风一般,作出最后的呐喊,也静静地作着最后的凝视,留下最后的眼泪。
跟“News from Home”不太一样,是“并非私电影的母亲的脸孔”。(这几年总是时不时想起小时候外公的家,记得天台的花和果、外公外婆的房间和书架,却记不起很多的细节:例如阳台是否有两个门,天台的栏杆的具体位置,哪些地砖有青苔……房子在建地铁二号线的时候拆了重建过,后来的房子跟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些东西都无从考究了。)
在我理解看来是另一种方式的《云上的日子》,与母亲聚少离多,用不一般的家庭录影,弥补不在一起的日子。[B]
很自然的生成,长时间的漫无目的。从机位的摆放和剪辑的方式来看,选择了空间而放弃了事件。有几个随意的运动镜头,把散落的场景缀连成整体。美感是被破坏了的,感受不到任何冲动与焦虑,只是与亲人、与世界的彼此陪伴。电影是什么?电影是那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人事风物。看得出来,阿克曼完全看淡了所谓的“电影感”,在生命的最后,她全身心地追求情感和自由。几次与妈妈的视频通话,那些爱让我的心都融化了。记忆消逝的时候,妈妈,请带上我。
一首写给空间与记忆的诗。四五分钟的静止画面令人震惊。房间角落里承载着时间之重的细节。来自荒野深处的风声。颤抖的光。母亲游移的身影与日渐消失的语言。对香特尔来说,凝视就是记住。
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日记,但这是电影日记。在感情面前,所有华丽的辞藻和浪漫的描述都是虚伪且脆弱的,正如虚构的事件更容易支撑人们脆弱的灵魂一样。你不愿意开口,他们谁都不理解,当你开口了,理解你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电影给了你40多年的生命,你却还给电影一个简单的日常。随唯一爱你的人安息。
风,沙砾,山峦。家的对面不是“公共”,no home movie至少有4种念法
树欲静而风不止,家如往日却无家;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
既有情深之处,亦有卑鄙之时
风中抖落的树 一望无际的沙 长久而静默的凝视 摄像机变成了眼睛 她的影像简直是如吃饭喝水般自然的表达 the dead body of everyday life 再贴切不过 此生过度漂泊 母亲去世后再无家
#HKIFF# "无家电影“的中文翻译是不对的,应该是”绝非家庭电影“,no "home movie"。全片是对那种刻板印象式的家庭电影的戏仿,探讨母女关系。有一些段落颇感人,但也有一些看起来漫无目的的镜头。(或许作为一个自杀女导演的遗作,应该被置于新的语境下考量)
This is no home movie; this is life movie. 从我你他她到News from Home到让娜·迪尔曼(才发现就是去年马里昂的女主怪不得莫名眼熟),总觉得我可以默默从她的作品中找到认同和同理心,有某种理解和connection. 如果来年还可以进图书馆就去继续补她~
#阿克曼回顾展#@艺海,如果这是阿克曼影展第一部片的话,可能就当成是一部谁都能拍的、轻松的、家有可爱老小孩的普通家庭录影带三星打好,然而在看完十四部阿克曼的最后时刻,几乎难过到泪目,这是一个就连聊熟人绯闻八卦都是苦难历史记忆,一个从奥斯维辛归来的波兰犹太人,一个与女儿视频电话都难以挂电话的母亲,“她在纽约在柏林过的怎么样她都不和我说”,联系《家乡的消息》《家书》《美国故事》和刚看的《那里》,香特尔也是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她独自忍受着莫大的痛苦煎熬,她做出和奥兹母亲一样的抉择甚至都不是意外,我想看得这么难过,是因为经过影展,了解了作者的作品生活经历家族历史(甚至她的眼睛),香特尔已经成为了我一厢情愿的朋友,所以这才是通过一次系统的、精心编排的影展了解一位创作者的全貌的重要理由
一部关于母亲去世的电影,重新审视母亲生前拍摄的家庭影像,毫无防备的就剪了这样一部电影,就像无意识状态下回忆自己的母亲,去面对自己一辈子绕不过去的母亲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话题。本该是只有母亲才有资格谈论的话题,自己却一再的越界去谈,这种一再的冒犯也深深的伤害了阿克曼自己。
时间在香特尔的镜头下如此具象,风、水、流逝的风景、家族的历史、衰老的母亲、变幻的光线、持镜者的呼吸。她如此长久而密切地凝视这一切,如同一场凝视时间的等待戈多,只等待死亡越来越近。